2023 年中国电影会好吗?电影人们在此直抒胸臆 -

2022 年,中国电影市场逆境之年。
年关已过,放眼宏观大局,全国票房在年末最后一天冲破 300 亿关头。十二月《阿凡达2:水之道》的上映,也尚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般成为救场的奇迹。虽然口碑还算令人满意,但截至发稿时,影片票房刚刚超过 10 亿,与上映前的乐观估计相去甚远,总排行榜上甚至不敌《侏罗纪世界3》及包括《人生大事》、《奇迹笨小孩》在内的本土制作,险些跌出票房榜前十。
过去一年中,海外影片在中国市场经历的失败是前所未有的,无论是奥斯卡系,还是超级英雄大片,都无缘与内地观众见面,如迪士尼般的巨头公司,甚至做好了“舍弃中国市场”的决绝准备。尽管市场主流席位统统让给了华语片,但比起外片的颓势,国产作品的表现也颇不尽如人意。2022 年仅有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、《独行月球》、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三部国产电影票房破 20 亿。从年头到年尾,除去春节档还算过得去的账面,其他包括清明、暑期、国庆等在内的重要档期均新片寥寥,票房也创下历年新低。
受到疫情影响最大、最直接的,无疑是产业下游的发行板块。频繁不期而至的封控让影院的经营变得异常艰辛,成都一家电影院推出“18 元午休套餐”。观众的观影积极性大大降低。与此同时,产业链条上的每个环节也都不得不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。这其中,非头部商业片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。
2022 年,海外重要节展上华语长片罕见地集体失声,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近几年创作者的困顿——融资步履维艰,拍摄受阻迟滞,发行无尽延缓,“黑马”、“爆款”、“出圈”等令人振奋的词汇,也许久没有在人们的讨论中出现了。
对线下聚集的谨慎态度,同样影响着电影节展的组织。曾经热闹非凡的迷影盛会或取消,或延期,直到夏天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举行,才多少标志着某种常态的恢复。但各主办方因为疫情而反复推倒重置计划,投入巨大人力、物力,导致很多电影节在开幕前就尽显混乱和疲态。原本热闹的创投与市场,在 2022 年多少显得有些门庭冷落。想要重拾旧日的元气,还需假以时间慢慢恢复。
中国电影市场曾经在 2010 年实现了百亿的突破。之后的十年,在引进大片、房地产和互联网热潮的加持下,这个数字迅速翻了六倍,2010 到 2019 年也被认为是中国电影最好的黄金盛世。然而,疫情给一切都按下了暂停,甚至是倒退键。“黑天鹅”的出现,让行业曾经积累下的问题成倍放大。2022 年的中国影视行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。而这一年也在人们不断地期待、失落、努力中转瞬而逝。
人们还来不及唏嘘上一年的困苦,2023 年便已急速而至。随着防控政策的调整,日常生活的回归,似乎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谈。而电影从业者,试图从他们充满身体感的叙述出发,倾听个体真实的声音,为具有建设性的理性讨论架设新的空间。
以下 WSJ. 与四位电影从业者——黄哲、木卫二、藤井谦、汪海林(按首字母顺序)的对话。

《WSJ.》:相较于往年,您 2022 年的观影状况(观影数量、去影院的频率、观影渠道、新老片的配比)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在您 2022 年的观片片目中,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国产新片是哪部,为什么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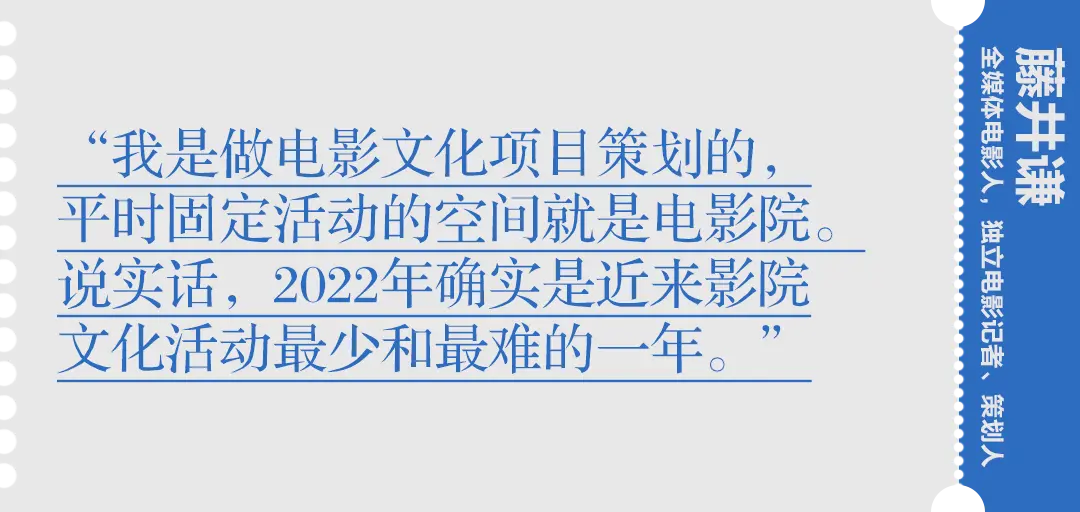
藤井谦:我是做电影文化项目策划的,平时固定活动的空间就是电影院。说实话,2022 年确实是近来影院文化活动最少和最难的一年。往年都会在影院搞 30-40 场左右的影迷文化交流活动,而 2022 年到目前为止只做了 12 场。我主要活动的区域是广东佛山,间或也会到广州来搞活动。虽然依旧有很多爱电影的朋友来支持,但整体的氛围、上座率和生态都是比之前有明显下降。
2022年我还保持着几乎每周去电影院的习惯,但电影的质量和可选择的空间,比之前相比有很大的变化。尤其是 10-11 月份,因部分地区疫情原因影响,再加上电影新片非常少,我两个月里只去了 2-3 次影院,其中一次还是看老片复映。
目前为止,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新作依旧是李睿珺导演的作品。这部电影绝对是内地影院 2022年度话题电影,没有之一。无论是导演的技法还是电影折射出来的某种生存现实,都是用心且考究的银幕表达。
木卫二:我所在城市上半年受防疫政策影响相对较小,包括《回南天》在内的几部都看了提前场,《七人乐队》、《神探大战》也是专门去看了粤语版。下半年,电影院需要 48 小时核酸证明,几乎没有新片上演,且多是滥竽充数,我就基本没去过电影院。看的最后一部院线片是《人生大事》。对我个人观影冲击最大的,还有电影节展的取消,状况不断。甚至于,2020 年我在影展看的片子,现在好多还没能上映。
2022 年印象最深的,是邱炯炯导演的剧情长片首作《椒麻堂会》。这部影片真正回到艺术创作的起始与原点,保有真实模样。《椒麻堂会》里的巴蜀,是你看完电影,才惊愕察觉其存在的昨日世界。舞台还在,但很寂寞。人间犹存,却很荒凉。想要重来,就趁此生。
黄哲:2022 年我的观影总量变化不大,还是在 150 部 - 200 部这个区间。只是往年,95% 以上的影片是在影院观看的。2022 年因为封控较多,大部分只能通过网络平台观看。现场观影还是集中在自己的“御三家”观影地——小西天(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)、Moma 百老汇电影中心和法国文化中心。自然而然地,观影数量以老片为主,占 90% 以上。少数的现场新片观看,则集中在北京电影节。
2022 年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国产影片都来自于我国台湾地区,《阳光普照》、《美国女孩》和《诡扯》,前两部比较击中当下。最后一部则让我发现“商业烂片”也可以拍出高级感。最重要的是,几部电影的讲故事和演技这两大底层能力集体在线。
《WSJ.》:因为节展和各项电影活动的或延期、或取消,行业聚会也不复往年的热火朝天,大家似乎都在为“吃饭问题”发愁。您周围的从业者现在都在忙什么?在您的观察中,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
木卫二:拥抱主流与主旋律的路牌,还挂在那里。一些朋友搁置了电影计划,转去拍摄网剧、短剧谋生。不少人想着跑路,已经付诸行动。由于事实上的阻隔和出行不易,克难时期,冷暖自知,无需了解太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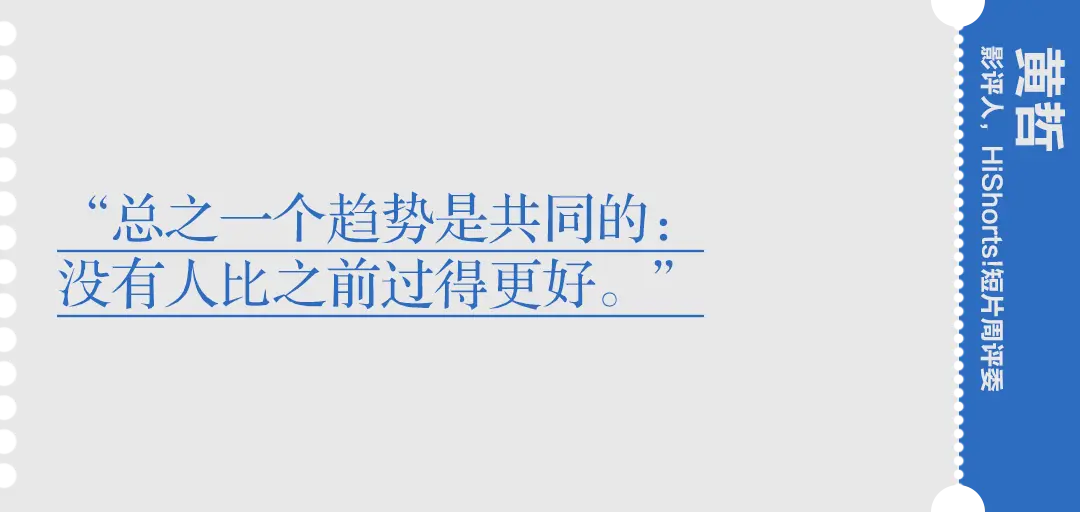
黄哲:家里不差钱的,可以继续学习、或是干脆苟着。有的去了相关领域,比如从事舞台工作,2022 年 10 月我去深圳蛇口戏剧节,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。还有去做教学、辅导艺考的——当然这两样如今一样萎缩。做主播也算相关领域吧?也有的干脆转行了,有的去卖保险、也有的去送外卖,希望这只是暂时的。总之一个趋势是共同的:没有人比之前过得更好。
藤井谦:作为最基层的工作人员,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。影院相熟的朋友能一直坚持的不多,即便一直坚持,面对日常运营的开销,以及各种不确定的因素,都还是忧心忡忡。转型与改变也是艰难的抉择,每当看到影院倒闭,影院改 KTV,影院转型午休服务,都满是苦笑无奈。但落在每个人身上的现实困境,还是需要面对的。有的朋友转行去做了微商,有的朋友去做了家装,有的朋友去做饮料生意……其实做什么的都有,最重要是能活下去。
大家对于改变是不排斥的,只是提到电影,都有一种难过的感觉。朋友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影院行业里苦苦坚持,他们和我一样,希冀着黑暗快点过去,哪怕回到去年的情境,我们还有很多电影看,我们还能为电影而躁动。我很佩服一直坚持的朋友,他们太不容易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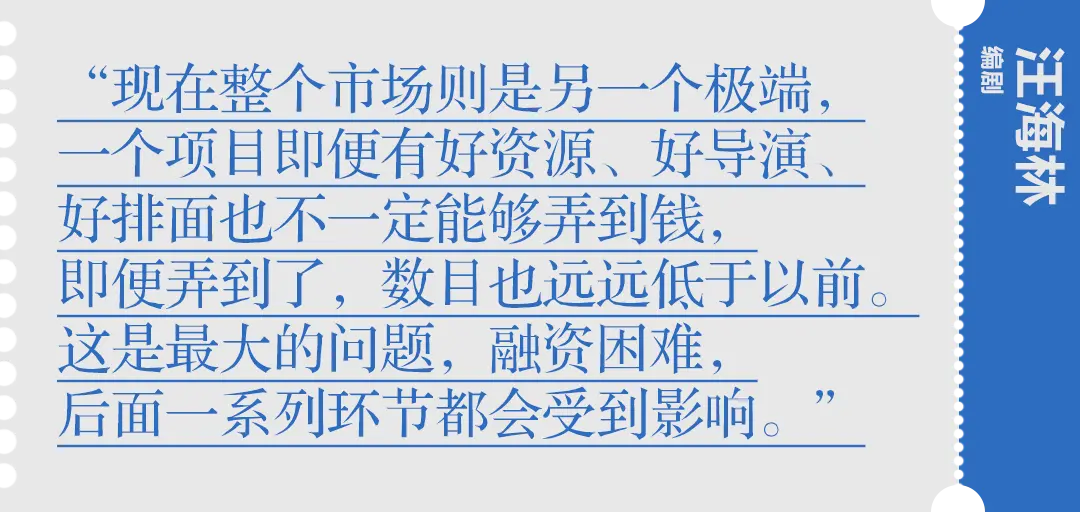
汪海林:疫情对于头部的编剧、导演、演员影响不是特别大。对于“腰部”的编剧、导演、演员影响比较大,他们的开工率、片酬各方面都受到影响。
在投、融资方面,影响则更为显现。我们知道几个大的头部公司的状况不是很好。这种情况下,资本投入减少,一定会让创作受到影响。2016、2017 年那样的盛况不会再出现,当时一个影视项目,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很多热钱。现在整个市场则是另一个极端,一个项目即便有好资源、好导演、好排面也不一定能够弄到钱,即便弄到了,数目也远远低于以前。这是最大的问题,融资困难,后面一系列环节都会受到影响。
《WSJ.》:“大陆影视行业正在经历寒冬”并非一个新鲜的说法,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工作者早已习惯了报团取暖,在寒冬中自救。那么,比起早些年的行业困境,三年来的疫情给影视产业开发、融资、拍摄、发行全链又带来了哪些新的冲击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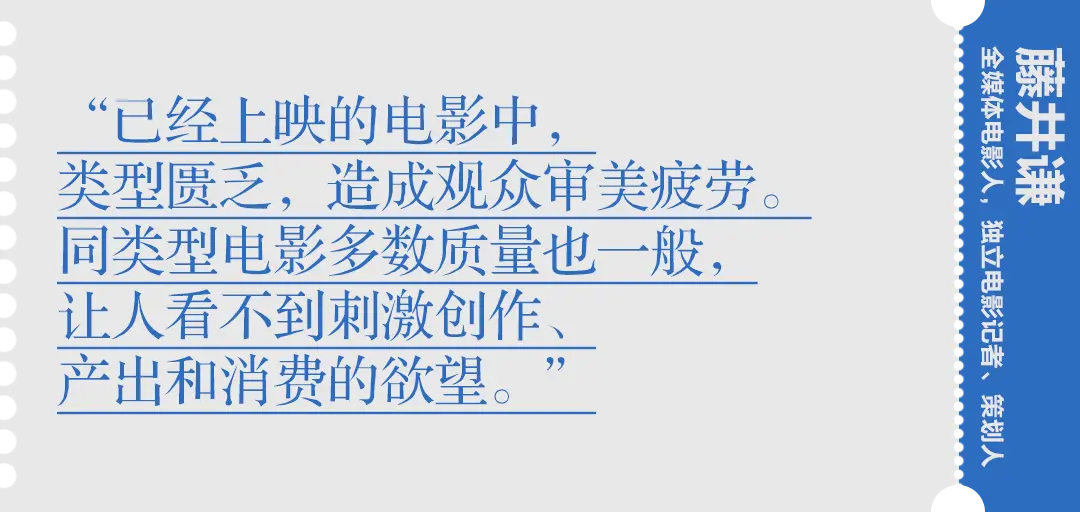
藤井谦:疫情带来的封控管理,对于到影院看电影的仪式感,势必造成很大的影响。特别是反复封控的情境之中,普通观众对于进影院都开始放低了兴趣。所以在封控阴影下,一些很值得去电影院看的电影,已经不再能吸引更多观众入场观看。再加上很多地区对于进入电影院有 48 小时核酸报告的硬性要求,直接阻止了更多人前往影院。
同时,从电影创作角度,很多剧组是否能够按时开机,都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。有个朋友 2020 年筹备开拍,因疫情影响,拍摄地几经改变,最终项目迟迟未能启动。已经上映的电影中,类型匮乏,造成观众审美疲劳。同类型电影多数质量也一般,让人看不到刺激创作、产出和消费的欲望。
上述多重角度细微的影响,让投资方对于电影带来的利润预估,产生了很大的疑虑。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,投电影不再是首要的挣钱方式,能吸引到的资方的项目愈发减少。
汪海林:就我个人的观察,2022 年整体来说市场的情况不好,有以下几个原因:首先是商业类型片不够。这个问题虽然是 2022 年凸显的,却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 2020 年至 2021 年创作储备不足形成的传导与显现。
其次是有号召力的电影商业 ip 表现欠佳,“唐探”系列 2022 年没上,“麻花系列”的票房也有下滑。最后,很多人认为影院不能够正常营业,是 2022 年中国电影票房不佳的原因。但我认为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。放开也不是能马上恢复的,这一点《阿凡达2》已经显现出来了,影片目前取得的票房,还不如在前三年动态清零的时候《长津湖》、《你好,李焕英》取得的票房高。影院放开不等于有高票房。放开对整个社会心理是很复杂的考验,公众在认为娱乐活动本身的风险没有那么大时,才愿意进电影院。而这个心理建设问题,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。

《WSJ.》:当我们在谈论当下的观众的时候,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:是一群被短视频更新了喜好的消费者,还是被疫情禁锢在特定空间中的饥渴者?影院经营不确定性的增加,流媒体的大肆兴起,该如何让这一届的观众重新为内容买单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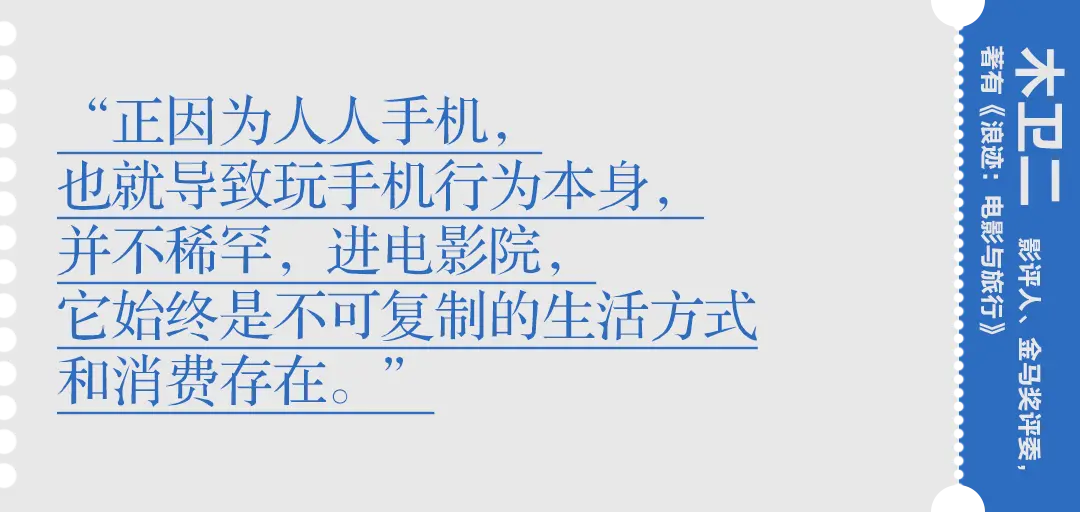
木卫二:在电影院没有恢复正常化之前,讨论观众去留取舍,本质上也无济于事。物理造成的阻隔,也强化了信息差异和屏障,容易放大误解,每个人自成孤岛。如果单就《独行月球》的投入产出,并不挑食,且乐于用脚投票的观众基础,依然存在。正因为人人手机,也就导致玩手机行为本身,并不稀罕,进电影院,它始终是不可复制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存在。我坚信于此。
黄哲:以我自己为例,按理说我已经不是 B 站的目标群体,但是这两三年发现 B 站对我越来越有用了,于是充了个会员,还接受了“考试”。尽管为某些不错的内容买单了,但不代表我认可现有的平台对内容的全部把握。很多影视资源还是寻求网络解决了,相比院线片关键剧情环节的缺失或消音等处理,还是或许不堪入目的网站贴片广告更能让我接受。
藤井谦:我觉得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,除了商业大片的加持,更需要行业有着宽松和自由的创作空间,用丰富的内容吸引观众,整合市场分类,带给大家脱离于手机端视频的审美,活络起电影文化体系,带动观众审美消费及思考,连带创作者和行业内对于电影创作能有新的思考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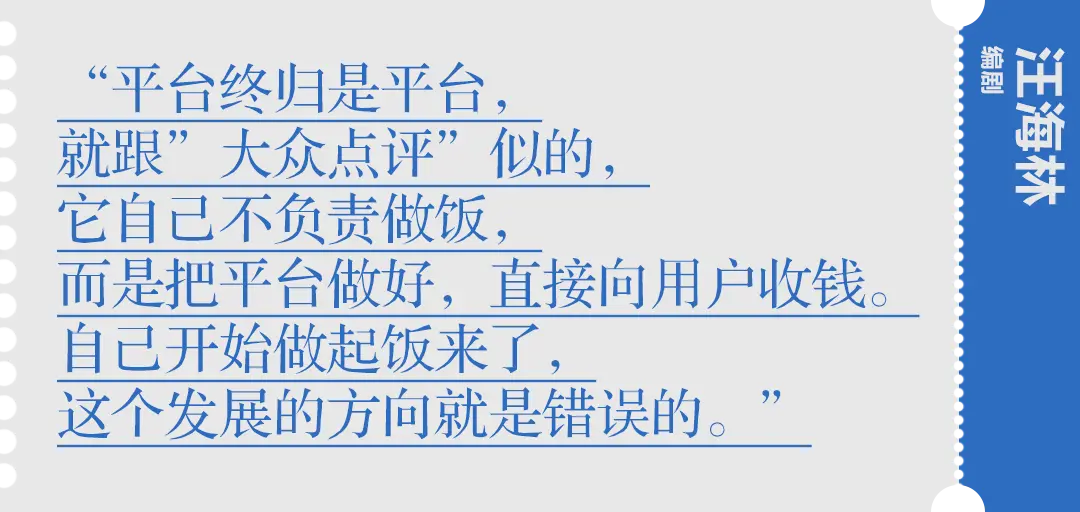
汪海林:目前,爱、优、腾三家,加上芒果 TV,他们原来的会员模式已经到达瓶颈,很难突破,甚至维持不了高额购片、运营和版权成本。所以我认为平台终归是平台,就跟”大众点评”似的,它自己不负责做饭,而是把平台做好,把评估体系做好,把播放体系做好,直接向用户收钱。自己开始做起饭来了,这个发展的方向就是错误的。
以前平台总爱挣“容易的钱”,什么叫“容易的钱”?偶像只要出来演,不管是什么,粉丝都愿意交钱。时间长了以后,他们就只会挣这个钱。因为靠偶像赚钱容易惯了,导致现在市场变成这样一个情况,真正想要靠内容,大家都没这个能力,这是几大平台共同的问题。
相比之下,电影创作更见真章,只要内容观众认可了,第一次拍电影的贾玲也可以问鼎票房冠军,不论资排辈。只有你内容行了,真正商业了,观众才会买票。这是最商业的一个模式,这是电视剧要向电影学习的地方。长剧集应该真正以内容为导向,通过内容来定项目,定投资,定播出,定收益。目前,这个模式依然没有建立起来,我很好奇几大平台谁能够率先实现尝试和突破。
《WSJ.》:因为种种原因,2022 年海外电影节上鲜有中国电影,旅行限制也让似乎让中国影人淡出了国际交流的舞台。这与亚洲其他国家,尤其是韩国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国际交流的缺失,会给中国电影人的心态,及华语电影的客观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?
木卫二:大陆蛋糕的满足饱腹感,导致文化输出与向外交流不再是必备选项。在随便拍一部电影就能拿下肥美票房的前十年,慵懒心态和优越感造就了电影人的舒适圈子。所以,无法加入世界游戏也不足奇。
黄哲:前阵子,世界杯足球赛正如火如荼地举行,看着以前和自己差不多、甚至还不如自己的亚洲同行已经可以赢欧美的前世界杯冠军了,中国足球从业者和球迷是啥心情,中国电影人和影迷应该也差不多吧……当然,两个领域都有多少心怀不平的,自然也就都有多少踏实躺平的。
藤井谦:电影是重要的交流媒介,在封闭的环境里,缺少了交流的乐趣,别说创作者,其实连观众都觉得无趣。大国的自信需要在各个方面展示给世界,电影是多重的窗口,这种窗口的展示能带给彼此一块天空,一个宏大的世界。我觉得这种缺少和空白,是一种遗憾的倒退,让人心疼。能走出去的,像是不复返的勇士。封闭带不来发展,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。
《WSJ.》:尽管 2022 年市场萧条,您是否可以举出一、两个依旧对于产业有启发性和参考意义的成功案例?

黄哲:我最近在给 HiShorts! 短片展做初审评委,第一次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、技术和创意都进入了短片和商业领域。许多参赛短片都是在网络平台出圈了的,既让自己的扎实功底和创意、创作能力得到展现,也为自己所服务的品牌赢得了不仅是商业市场,更是普通观众群体里的美誉度。连商业短片都如此,以故事长片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市场更是这个道理:观众不是不能接受商业等因素,只是首先还是需要好故事。
其次,创作者需要把观众放在平等的地位上,而不是喂饭或倾销。最后,我认为有一点和疫情大背景有很大关系: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和共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。
《WSJ.》:网大、剧集项目的开发,在疫情前就已经得到行业的重视。随着短视频和流媒体进一步占据人们的生活,您是否认为传统影视行业人才与资金是否会加速向该板块流动?在此相对新型的创作领域,海外有无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?
藤井谦:网络已经是目前行业板块流动的一个主体了,由此加大了大众对于影院观影的犹豫感。虽然网络确实比较活络,但也是降低了大众对于大银幕的需求,电影似乎被网大和剧集渐渐排挤出去了,想想还是挺遗憾的。虽然网飞等流媒体确实给电影及剧集带来了不错的平台及发展经验,我还是想强调“电影院”空间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。

《WSJ.》:相比长片创作的迟滞,近年来华语短片倒是在世界上走得很出彩。如何才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势头?短片背后大多是初入市场的青年创作者,他们需要怎样的扶持和帮助?
木卫二:修桥铺路无骨骸。电影业的全盘崩溃,在东亚地区多次上演,只不过大陆所遭遇的,似乎更加摧枯拉朽。对于年轻一代,尤其是留洋归来的创作者,抛弃这些幻灭、光环与负累,轻装上阵,依然会有成绩。新世纪初,业余电影的号角,一个人拿起机器的冲劲,依然适用于今天。
黄哲:其实想要“维持”本身就不是对待新生事物最好的方式,想想什么才要维持?勉强得来的局面、甚至是日薄西山的情况。哪怕小树苗也先让放手让它长,直到真正开始疯长或者到了结出丰硕果实前,才考虑修剪。
比起大量的以“资”鼓励(当然近年客观条件也不允许),它们也许需要的是有限(尽量基本够用)的资金扶持、(相对)无限的创作空间,和大环境的满满善意。最后一点也许最难,因为没有相对好拿捏的尺度标准。但起码要多给他们机会,而不是说一开始没人认可,甚至只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就把门关上了——哪怕扔在角落里给点阳光雨露,让他们自生自灭也好呀。就算不是灵芝的料、长出蘑菇来也是收获,不是吗?
藤井谦:保持宽松的创作空间,给年轻人更多的平台,让他们能找到投资人及合作伙伴,去尽情尽兴的展示,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
《WSJ.》:当下的电影教育课程、培训层出不穷,反应了行业储备人才的强烈诉求。那么,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,如今的电影教育如何自我迭代?面对有意进入影视业的新生代力量,电影教育工作者又需要让他们做好哪些准备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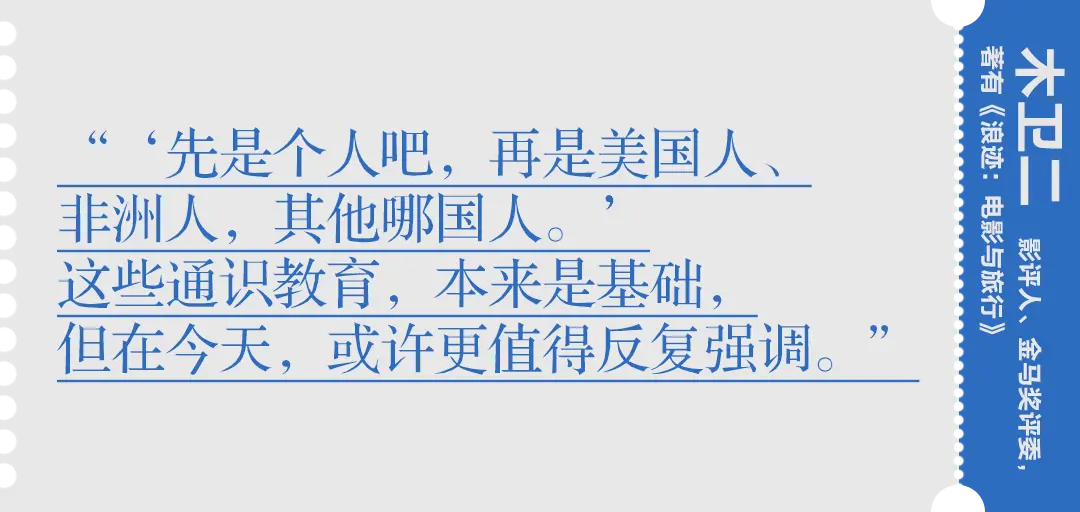
木卫二:所谓教育,是从人出发。先认认真真,踏踏实实做个人,再考虑做电影。而没有一种电影,是制作出来,专属于中国的。如同是枝裕和纪录片《当电影映照时代:侯孝贤和杨德昌》,杨德昌说,“先是个人吧,再是美国人、非洲人,其他哪国人”。这些通识教育,本来是基础,但在今天,或许更值得反复强调。
藤井谦:给学生们创造平台、机会和窗口,这是在我来看电影教育能保持吸引的重点所在。
汪海林:在电影教育方面,还要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,也就是说,编剧不能只懂编剧,也要懂一些市场、制片和制作。导演也要懂一些技术,和更多复合型的知识结构。
在整个创作训练上来讲,除了现实主义,要对先锋派、对商业类型的创作都要熟练的掌握,不能只掌握一种,创作者对先锋叙事、商业叙事都要熟练地掌握,这才是整体的趋势。
《WSJ.》:陈可辛导演在釜山宣布成立 Changin Pictures,给华语创作者带来了颇大的震动。泛亚洲合作是否会成为大陆影视行业的又一条出路?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挑战?
藤井谦:这是很好的一种视角及创作趋势,我觉得这会成为一部分行业人员的出路。但这条出并不能代表全部,并于普通创作者来说,创作环境的限制,还是从业者最大的束缚。
汪海林:我觉得对陈可辛来说是有利有弊,他的走出去,本没问题。但是如果变成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话,会使得他个人的发展,包括这个模式产生一些变味。
如果你问看好这个模式吗?我个人觉得,这个模式在创作上肯定是有益的。但是在市场上,丢失中国大陆,很可能导致产出的作品不够商业。我们电影一度是全球第一市场梯队,跟北美轮流坐庄前两名。如果这个模式意味着丢掉大陆市场,也许会是巨大的损失。
